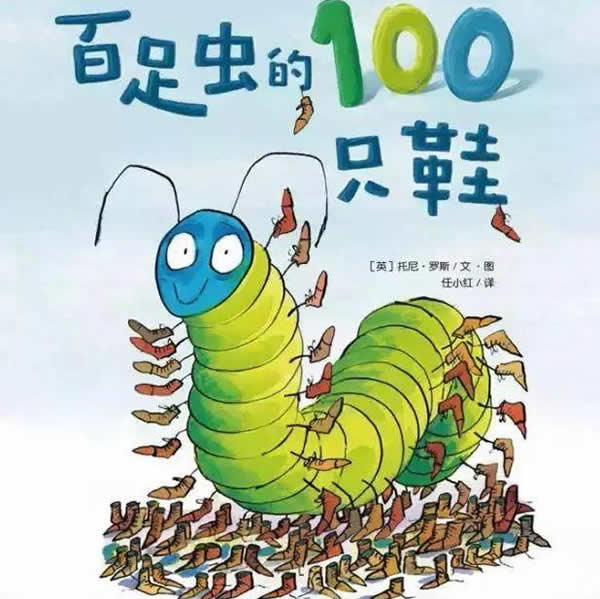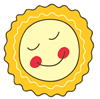睡前故事红奶羊
红奶羊
大公狼黑宝躲在一棵被闪电灼焦的枯树后面。一双饥饿的狼眼紧盯着前方。那里是神羊峰通向尕玛儿草原的最后一个山坳口。一会儿喀纳斯红崖羊群将要从这里通过。
鲜嫩的羊肉对狼来说,无疑是一顿美餐。但今天大公狼黑宝并不打算来吃羊肉。昨天夜里,黑宝的妻子,小母狼蓓蓓为它生下两只小狼崽后,不幸大出血死了。没有奶水喂养的两只小狼饿得连声音都叫不出来。着急的黑宝试图用咬烂的兔肉喂它们,可小狼崽还不会吃东西。今天早晨,那只黄毛狼崽已经饿死了,另一只黑毛狼崽也饿得半死,别的母狼又没有帮它喂后代的天性。黑宝急得没办法,终于决定抢一头奶羊来喂它的狼崽。
这时,红崖羊群从山坳口出来了。黑宝仔细地观察着走过来的每一头羊。
忽然,它发现,一头肥硕的年轻母羊落在羊群队伍的后面。母羊浑身金红的羊毛亮闪闪的,腹下四只饱饱的奶子像熟透了的柚子,这正是它理想中的奶羊!看准了目标,黑宝从枯树后一跃而出,扑向红母羊。可怜的红母羊还没反应过来,就已经被狼叼着耳朵抢走了。
这头红母羊名叫茜露儿,本来它是不会被狼抢走的。因为茜露儿不是普通的母羊,它是羊群中最美丽的母羊,是头羊古莱尔最宠爱的妻子。然而,它却十分不幸,昨天深夜,它在神羊峰的溶洞分娩了。可小羊羔一生下来就死了,幻想着做妈妈的茜露儿伤心极了,直到今天早晨,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茜露儿,神思恍惚地落到了羊群后面。它离开了头羊的保护,因而成了狼的俘虏。
突然的惊吓和恐惧使茜露儿昏了过去。昏迷中,它仿佛感到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拨弄它的眼皮。它睁开眼来,吓得心惊胆颤。面前一只凶狠的狼正用舌头舔它呢。茜露儿吓得惊跳起来,刚站立,右腿一阵钻心疼痛,原来狼把它的后腿咬断了。黑宝为了防止它逃,把它变成了瘸腿羊。茜露儿被黑宝捉进了狼洞。
正当茜露儿惊恐之时,黑狼叼来一只黑乎乎的小狼崽,放在它的腹下。
茜露儿明白了,黑狼为什么没有吃掉它,是因为要它当奶羊。茜露儿不愿意让自己的乳汁流进小狼崽的嘴里。它厌恶地扭转身。黑宝凶恶地嚎了一声,把牙齿咬得“格格”响。茜露儿知道,如果它再拒绝,自己的喉管就要被咬断。孱弱的茜露儿被迫成了小狼崽的奶妈。
小狼崽在羊硕的乳头下贪婪地吮着茜露儿的乳汁。不知怎的,茜露儿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松弛下来。它是头一次哺乳,没想到感觉竟是这样奇妙,这样飘飘欲仙。它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小羊羔,仿佛感到自己的宝贝在吮着乳汁。茜露儿对狼崽的厌恶随着初次哺乳的快感消失了。但很快它又仇恨起狼来,狼和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呀,茜露儿的心里矛盾极了,于是,它想逃跑。
可是,茜露儿没能逃出狼窝。黑狼紧紧地盯着它。只让它有一点到洞外草地上吃草的自由。有一次,它趁黑狼外出捕食,想悄悄逃走,但狡猾的狼早就作好了防范,在布满荆棘的洞口,茜露儿被黑狼发现了,凶狠的黑狼在它快要伤愈的右腿上又咬了一口。这一回,茜露儿瘸得更厉害了,它逃不出去了,可怜的茜露儿由喀纳斯红崖羊群尊贵的皇后,一下子变为黑狼的阶下囚,它内心无比痛苦。它思念着羊群,思念着神羊峰下和平、幸福的生活。
一眨眼二十多天过去了。小狼崽在茜露儿充沛的奶汁喂养下,日渐强壮,黑毛油亮,胖嘟嘟像只肉球。小狼有了一个名字叫黑球。黑球年幼不懂事,它把茜露儿当作了自己的妈妈,整天偎在它怀里撒娇。最初它很不习惯,而且非常厌恶黑球,但渐渐地,出于动物母性的本能,茜露儿开始与小黑球进行感情交流了。虽然它表面对黑球很冷漠,但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温情。但它压根儿也没想到,它和黑球之间的感情,会刺激黑狼,想提前咬死它。
黑宝很耽心黑球会被母羊异化,没等黑球满月,它就决定当着黑球的面咬死茜露儿,让黑球在血腥中成为一条真正的狼。
这一天,黑宝把狼牙磨得很尖,太阳落山后,它正准备扑向红奶羊茜露儿。可就在这时,猎人带着猎狗发现了狼洞。猎人明晃晃的猎枪对准狼洞。
为了保全小狼崽的生命,黑宝不顾一切地冲出洞口,它要把猎人引离狼洞,但无情的猎枪击中了黑宝的脑袋,顿时倒地气绝。
洞外的枪声震醒了茜露儿。大黑狼死了,它可以放心大胆地回神羊峰了。
茜露儿激动地奔向草坪,它可以见到头羊古莱尔了!忽然,它的脚被黑球绊了一下。黑球蹒跚着,跟在它身后。茜露儿一脚把它踢出一丈多远。小黑球趴在地上呜呜哀叫。茜露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但身后黑球柔弱的哀叫、委屈声,触动了它的母性。这只没爹没妈的小狼崽除了吃奶,还不会干别的。
真可怜!茜露儿的心软了,它想,再喂它一会儿,等断了奶再离开它。于是,茜露儿带着黑球离开狼洞。它们登上日曲卡雪山上的一座断崖,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窝。
转眼又是三个月过去了。黑球长出了尖利的狼牙,体魄也很健壮,它长成一条半大的幼狼了。虽然黑球是狼,但它跟着羊妈妈,从来没扑食过活动物。茜露儿想把黑球培养成具有羊性的狼。它叫它学羊叫,黑球叫得虽不像,但“呕——咩..”也不像狼嚎那么难听。
但是狼毕竟是狼,黑球终于显出狼性了。一天,黑球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羊,它迅速扑过去咬断了小羊的喉管。茜露儿看得心惊肉跳。它终于明白了,狼是改不了凶残的本性的。黑球已经断奶了,茜露儿决定赶紧离开它。
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茜露儿趁黑球睡熟了,悄俏起来。黑球躺在断崖的平台上,茜露儿心想,如果就这样离开黑球,等黑球长大了,一定会成为一条恶狼的。再说它喝过自己的奶,简直是一条可怕的披着羊皮的狼呀。
茜露儿决定把黑球踢下悬崖,除掉后患。可是,就在这时,一匹狡猾的豺悄悄摸上了断崖。它想吃掉红母羊。黑球惊醒了,为了保护奶妈,它和强大的豺拼搏了一阵,最后将豺打跑了。但黑球的肩上被豺咬掉了一大块皮。黑球累坏了,很快又倒在奶妈身旁睡着了。这时,茜露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黑球推下深渊。但它放弃这个血淋淋的念头,悄悄地走了。
茜露儿借着月光,翻过一道道山梁,又回到了喀纳斯红岩羊群里,成为一头美丽的羊皇后。它整天跟着头羊古莱尔到尕玛儿草原觅食,在神羊峰憩息。渐渐地,它把自己波黑狼抢去当奶羊的传奇经历忘掉了。
第二年的春天,茜露儿和古莱尔又添了一公一母两只羊羔,公的叫沦夏,母的叫珊瑚。茜露儿和古莱尔非常爱护它们的孩子。一家四口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。要不是没有那只凶暴的猞猁闯进羊群,茜露儿会永远对古莱尔很温顺的。
那是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闷热下午,羊群穿行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间。
忽然,一只猞猁窜进羊群,朝小羊羔珊瑚扑去。珊瑚吓得躲进古莱尔腹下。
古莱尔本可以用锋利的羊角吓退猞猁的进攻,但古莱尔抛下珊瑚,自己逃命去了。茜露儿带着沦戛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,可怜的珊瑚眼睁睁地被猞猁叼走了。茜露儿的心碎了,它卧在草丛中,伤心地流着泪。
过了一会儿,古莱尔也垂着脑袋慢吞吞地走近茜露儿。它很伤心,但一点也不羞愧。这位茜露儿忽然想起大黑狼为保护黑球,只身冲向猎人的壮举。
它感到很吃惊。自己怎么又会想起黑狼和黑球呢?心烦意乱的茜露儿没有理睬古莱尔的安抚,它粗暴地推开了古莱尔。
茜露儿把所有的爱都用在论夏身上。它要把沦戛培养成一头勇敢的,负有责任心的新型公羊。每次羊群在沼泽地穿行,茜露儿总让沦戛走在最前头。
暴风雨来了,别的羊都躲在山崖下,沦戛却要在霹雳声中散步。在茜露儿的训练下,沦戛的胆子越来越大,有时,碰到了狐狸、狗獾之类的小型食肉野兽,沦戛开始壮着胆子主动出击了。不久,沦戛的头顶上长出一对锋利的羊角。
有一次,羊群路过一片乱石岗,发现一匹狰狞的狼倒在怪石背后。虽然是一匹死狼,但羊群还是惊恐地乱叫起来。沦戛在茜露儿的带领下,敢于用羊角刺破死狼的肚皮。沦戛由怯懦的小羊羔变成一头勇敢的公羊。
茜露儿为沦戛感到骄傲。它想,等沦戛将来娶妻生崽后,一定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儿了,它不会像古莱尔一样,只顾自己逃命的。
沦戛越来越健壮,它的毛色红亮,一双羊角威武雄健。它受到羊群的尊重,它的地位几乎和头羊古莱尔一样了。
但是,再勇敢的羊也不是狼的对手。一场灾难就要发生了。
这一天,大地盖着厚厚的雪,茜露儿和沦戛并肩走在羊群的前面。忽地,雪地里窜出两只恶狼,茜露儿不亏在狼窝里生活过,它机警地向身后羊群发出警报。羊群拼命地向后逃。一只土黄色的母狼张牙舞爪地向茜露儿扑来,另一只毛色黑亮的公狼也冲到它和沦戛身后,切断了它俩的退路。
整个红崖羊群趁机逃进茫茫草原。只有茜露儿和沦戛还在和狼周旋。眼看着黄母狼就要扑到面前了,茜露儿突然一头向黄母狼撞去。黄母狼措手不及,它怎么也想像不到,一头红崖羊竟敢和它搏斗,历来都是羊看到狼吓得发抖的啊。正当这只黄母狼吃惊的当儿,茜露儿猛地一蹿,跃过沦戛和黑公狼,没命地向峡谷深处逃。沦戛紧紧跟在它身后。
茜露儿慌不择路,一头钻进了鹭鸶谷。这鹭鸶谷又细又窄,进口能容下两头羊并肩走,而到了出口,仅能容得下一头羊通过。出了鹭鸶谷就是神羊峰了,到了神羊峰就能脱离狼爪了。
当茜露儿快跑到出口时,它紧张起来。因为紧随其后的沦戛不能和它同时通过出口,如果沦戛和它相互推让,那么狼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都吃了。
沦戛在茜露儿的身后,茜露儿宁愿自己去死,也要换取沦戛的生!茜露担心沦戛会因为让它先过出口,而将自己的羊角刺向恶狼,那样沦戛会被狼咬死的!正当茜露儿在紧张的思考着,突然,它的身体被猛烈地挤撞了一下。它一个趔趄,跌倒在岩壁上,肋骨几乎要被撞断了。它以为是狼追上来了,可定睛一看,两匹狼还在后面紧追着。是沦戛撞倒了它!沦戛为了先钻出出口,把它撞倒了!沦戛壮硕的身体钻出隘口,头也不回地奔进了神羊峰。
茜露儿受到了两匹恶狼的前后夹击,它已陷入绝境,必死无疑了。黄母狼冲着它嚎叫一声,茜露儿并没有被吓倒,它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其实,当沦戛把它撞倒的那一瞬间,它的心已经死了,它平静地等待着死亡。
一股尖啸的西北风刮过,黑公狼突然拼命地扇动鼻翼,朝母狼发出一声古怪的低嗥。本来已经准备扑咬茜露儿的黄母狼不解地朝黑公狼望去。黑公狼慢慢地走近茜露儿,突然发出“欧..咩..”的叫声。这非狼非羊的叫声,使茜露儿的心抽搐了一下。它也探出羊鼻子贴近黑公狼仔细地嗅闻了一遍。透过血腥的狼味,它闻到一股熟悉的羊奶气息。啊!是黑球!它的肩上还留着与豺搏斗留下的伤痕。黑球!两年不见,黑球已经完全长成一只威风凛凛的大公狼了。
黑球蹲在它面前,眼里的杀气隐退了,它乖得像只羊羔。
“欧——”黄母狼突然凶猛地叫起来,它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的丈夫竟和羊粘粘乎乎。它向黑球发出警告。黑球眼里闪烁的相逢喜悦很快都消失了,它后退了一步,用身体挡住了黄母狼。黄母狼不愿放过这美味的羊肉,它愤怒地推开黑球向茜露儿扑来。
茜露儿并没有指望黑球能救它。它知道狼的天性,再说这两只饥饿的狼在雪地里一定等了很久了,如今又追赶到这里。难道还会放过自己?
黑球仍然挡住黄母狼。黄母狼气得扑到黑球面前,朝黑球的腹部咬了一口。它想迫使黑球让道。黑球像座石雕,既不回击,也不躲让,它的腹部流着血。黄母狼到底还是心疼自己的丈夫的,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嗥了一声,转身飞奔出鹭鸶谷。
黑球面朝着茜露儿,一步一步朝山谷外退去,退了很远很远,它才倏地转身,追赶自己的狼妻去了。
茜露儿仍呆呆地站在岩壁前。它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狼口逃生,还是该悲哀自己被儿子抛弃。它再也不愿回喀纳斯红崖羊群中去了。它抬头眺望白雪皑皑的神羊峰,传说峰巅上住着一头英勇无比的大公羊,它既有温顺的羊心,又有猛兽的胆量。它能保护所有的羊群。茜露儿要去寻找它。茜露儿迎着凄迷的雪尘,艰难地向神羊峰的顶巅攀登。
它相信一定能找到它。
人生故事红琵琶
列车在车站喘了口气,便闷头又朝前跑去。他实在坐着无聊,那本杂志他看了八遍,几乎都背下来了。想跟邻座的人聊聊,可一看邻座衣后领的油渍,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想借机回忆自己的生活,可满脑子都是空白,他显得有些悲哀。窗外还没有绿色,黄黄的,干干的,令人心烦。
这时,车厢门口闪出一张青春迷人的脸,两颗活灵灵的眸子,白色的防寒服,亮晶晶的高腰皮靴。飘逸,清秀,高雅。如一泓清泉,似一缕春风。背后背着一把琵琶,用红绒制成的套,细致精巧。这……能挤挤吗?她的声音仿佛一串铜铃摇响,清脆,动人。他慌忙移了移,宁肯自己委屈,腾出一大块地方。沉默了一会儿,他把那看了八遍的杂志又捧起来翻弄着。
您也懂音乐?她歪着头,惊喜地看着他。
他搁下那本封面庄重的《中国音乐》,表情有些腼腆,但脸色很平静地说,我是指挥,民族乐团的。他的声音优美,浑厚,似敲响大钟。
太巧了,我刚从音乐学院毕业,弹琵琶的。她递过一个黄澄澄的大鸭梨,挂着甜汁,渗着喜悦。他接过大鸭梨,然后,熟练地用小刀削着,削掉了长长的一截儿皮,然后中间一切,另一半递给她。
姑娘轻轻咬了一口,歪着脑袋问,您这是到别的城市指挥去吧?
不,是到外地去讲课。
姑娘羡慕地问:您都指挥过什么曲子?
哦,多了,有《春江花月夜》《春节序曲》……他说出一大堆曲名,那两只手臂下意识地摆动几下,小刀似乎成指挥棒,头发一甩一甩的,颇似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。也有我的曲子,刚刚在全国比赛拿了一个铜奖,成绩不太理想,但我已经尽力了。说到这儿,他停顿一下,问,你呢?他非常愿意看她的眼睛,清澈,无任何杂质。像碧波荡漾的湖泊。他真想去摸一下,让湖泊泻出潺潺的清水。他很少这么近距离地和一个漂亮女弦子说话,挺有意思的。
我最爱弹《十面埋伏》。我给您弹一段……姑娘迫不及特地从身后长长的带子里取出一扇琵琶,然后调好弦。周围的旅客围拢过来,觉得很好奇。
他没想到姑娘这么爽快。
她取出的琵琶也是红色的,像一团火胜过牡丹。琵琶竖起来,像一棵白杨树,挺拔俊秀。她像演出一样稳了稳情绪,不好意思地对他嫣然一笑。蓦地,拨响琴弦,琴响处如千军万马,战鼓轰鸣。周围的旅客被这乐曲弄醉了,痴痴地听,愣愣地看。他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,脸上的表情很淡。
您给提一提?她眨动着一双真挚的眼睛。
哦,力度还欠些,有的和弦不准……你的右手不协调,另外,这首曲子不是光靠高亢,它有伤感的地方。很多琵琶演奏家都忽视这点,弄得战争的味道很浓。你可能不太了解这首曲子的历史背景,只是在模仿别人的技巧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,突然他停住,他发现姑娘的眼光里充满了崇拜。他的心在颤抖,很久没有的颤抖。他说。你的第四根弦不准,偏低。
姑娘犹豫地试试,果然偏低。她说,我的耳音很准,教授都夸奖过我,可您的耳音比我们教授的都灵验。
到了一个大站,他和她全都站来下了车。
你也在这儿下?他有些紧张地问。
我分到这儿了。
是吗?他没打招呼,匆匆随着人流走了,那背影有些抖。
她也走了,身后那簇红琵琶外套格外引人瞩目。
她上她所在的团报到了,在排练厅,她看见一个庞大的民族乐队在演奏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指挥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,据说是很有名望的。在乐队一角的打击组里,他在卖力气地舞动着大镲。额前挂满了汗珠。姑娘迟疑了片刻,还是笑着朝他走去……
人生故事红皮包
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混混儿。我知道他来自于怎样的环境———一个聚集着帮派、吸毒者以及满是暴力的低等住宅区。他说话时带着街头的痞气,他的行为和平常人也不大一样。他走路总是摇摇晃晃的,像一个被击败了的拳击手,而他的面部表情就像银行地下室坚硬而呆板的铁门。在我看来,他长得过于粗壮,他似乎总是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暴躁,以便自己能够适应康复医院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工作。
我们医院的病人,大多数是来这里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。他们来这儿,因为残疾,或是重病,或是神智混乱,要不就是身体机能已经衰竭,丧失了活动的任何能力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清晰的思维,绝症和残疾使他们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。尽管这似乎很残忍,但对他们来说,却完全无关紧要。
玛丽B就是他们中的一个。护理人员喊她“玛丽B”,因为她是病房西区4个玛丽中的一个。她94岁,脆弱得就像一张飘荡的蛛网。她的丈夫和姐妹们都已先她而去,如果她还有孩子,他们也很久没有管过她了。只要她醒着,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手舞足蹈,几乎没有安静下来的时候。
玛丽B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: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。她整天整夜不停地找,除非她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。她会出门穿过医院的林阴路,进入男病房区,钻进洗衣房或者厨房,没头没脑地寻找,并且从不放弃。当别人干涉她,她就要求护理把她的轮椅推到大厅,她会一直呆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。
“能借给我一把梳子吗?”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这样说,“我的梳子丢了,它在我的红皮包里。我的钱也丢了。我的皮包在哪儿?”
每天,她都重复同样的事,最后玛丽B的询问变成了院子里的噪音———就像手推车装载着滚烫的盘碟经过门厅,或是空调发出的嗡嗡声,又像是对讲机里发出的静电噪声。
我们都知道她根本没有皮包。但尽管我们都特别忙,偶尔还是会有人停下来,带着关心和善意聆听她的唠叨。当然,大多数人都会安慰她两句:“好的,玛丽,如果我见着你的皮包,我会给你拿回来。”
我们大多数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———只有一个人除外。
我从不认为肯尼会有耐心停下来听玛丽B念叨,但奇怪的是,他总是能跟玛丽B在一起说着些什么。
他要做什么?我很担心,我观察着。我的第一个猜测是,他是想偷些麻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才在这里工作。我想我碰到了一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人。
当玛丽B每天叫住他问皮包,而肯尼都答应帮她找时,我的猜疑更不断加深了。我推断出肯尼的某种计划也许要把玛丽B也搅在其中。我想,他可能是想把偷到的药藏到玛丽身边,然后他的同伙再溜进来把药从医院里偷出去。我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,因此我特别加强了对药品分发部门的安全防范工作。
一天下午,在晚餐之前,我看到肯尼往大厅走去,手里拿着一个杂货店的塑料口袋,它看上去鼓鼓囊囊的。
就是这个袋子,我告诉自己,我从桌子后面站起来,悄悄跟了出去。我从后面盯着他,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证据,于是我停在大厅里一辆洗衣车的旁边,洗衣篮高高地堆在车上面。
这些洗衣篮正好挡住了我的身体,但是我仍能清楚地看到肯尼大步走向大厅,朝玛丽B的轮椅走过去。
他走到那里,突然转过身来,朝四周张望。我躲开他的视线,看到他紧张地窥视着整个大厅。他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要干什么。
他拿起塑料袋。我的心提了上来,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……直到他掏出一个红色的女士皮包。
玛丽B瘦骨嶙峋的手猛地抬起来,在脸前做了一个惊异和高兴的手势,然后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抓住面包那样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。玛丽B紧紧抓住那个红皮包,她把它握在手里,仔细地打量着,然后把它紧贴在她的胸口,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地轻轻地摇晃它。
肯尼转过身来,再次飞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。确定周围没人看他以后,他弯下身,打开皮包,把手伸进去,然后他从包里给玛丽B拿出一把红色的梳子,一个装硬币的小钱袋,还有一副小孩玩的玩具眼镜。
玛丽B的脸颊上流下了高兴的泪水。我认为她是因为高兴而流泪的。
泪水也流在了我的脸庞上。
肯尼轻轻地拍拍玛丽B的肩,把塑料袋卷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,然后,他离开了大厅继续去做他的工作。
我走回我的桌前,坐下来,想起以前对肯尼的怀疑,心中充满了愧疚。
下班的时候,我站在平常护士助理上下班经过的门旁。肯尼带着他的上衣和收音机,蹦跳着走过大厅。
“嗨,肯尼,”我说,“还好吗?你喜欢这个工作吗?”
肯尼惊奇地看看我,然后耸耸肩。“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工作。”他咕哝着说。
“护士是一个好职业,”我强调,一个主意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,“唔,你可曾想过去上大学,得到一个正规的护士学位?”
肯尼简直不敢相信。“你在开玩笑吗?我不可能得到那样一个机会的。除非这个护士课程是免费的,否则我不可能得到这个机会。”
我知道这是事实。肯尼放下他的收音机,穿上外套。“上大学对于我来说,是一个奇迹,”他说,“我爸在圣昆顿监狱,而我妈在吸可卡因。”
我紧紧咬住牙齿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,仍然保持微笑。“奇迹总会发生的,”我告诉他,“如果我能想法资助你的学费,你愿意去上大学吗?”
肯尼不敢相信地盯着我。在这一刻他不再像一个混混儿了,我期待着他的回答。“当然!”这就是他所说的,但这已经足够了。
“晚安,肯尼,”当他握住门把手时,我对他说,“我相信,有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到的。”
人生故事想红
早上,男生跟女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。女生是班长,是男生的心上人。男生暗恋女生,女生却不知道。男生是个沉默的小男孩,女生漂亮大方,待人真诚友善,吸引班上一众男生,排队追逐。女生时常跟一些男生去游山玩水,坐在别人摩托车后座的女生,俨然成了别人的女朋友,男生退缩了,觉得没希望了。
过了N年,女生上了大学,男生在工厂打工,男生每次打电话给女生,就匆匆挂了电话,生怕女生听到他急促地心跳声。男生和女生相约再见的时候,已成了一对亲密恋人。男生和女生躺在一张床上,男生翻身想要了女生,女生拒绝,说:“等我们结婚好吗?到时候什么都给你。”
中午,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,那是他妻子刚为他生的女儿,妻子不是当初自己喜欢的女生。女生也嫁人了,嫁给一个很有钱的土豪。出门开大奔,吃饭上高级餐厅,金银饰物戴不完。唯有一问题:土豪年纪上去了,早些年发达后,睡了几条街的女人,二奶从别人的老婆到大学生,纵欲过度的结果是——性无能。
女人容忍土豪去外边偷腥,但不能容忍夫妻没有生活,一气之下,闪婚闪离,土豪分给她几百万的青春损失费,女人始终忘不了她的情哥哥,男人呢?家庭幸福美满,貌似早已经忘记他当年苦苦挽留的女人,但还是留不住女人想嫁土豪的心。
傍晚,男人成了一个老头。他在厂里光荣退休后,成天在市中心的老干部活动中心遛狗。妻子比他先走一步了,他难过心酸。女儿也嫁给一老外,移民到美国做全职太太了,剩下老头一个人孤苦伶仃靠工厂那点退休金养老等死。
他想起他的恋人小红,于是托人寻找,终于在另一个城市某高校找到正在做清洁工的老太太。女人早已不复当年模样,却保持着较好的身材和面容,只是皱纹开始在她的脸上刻画了。老头跟老太太见上一面,相拥而泣,各道衷肠。
原来老太太拿着土豪给的几百万青春损失费,先后投资过几个大型超市。结果没多久,钱财都被那些以恋人身份与她合作的男人骗光了,那些人从此音信全无。她也想过去找老头,但那时候老头身边太太健在,所以不想去破坏老头的家庭。这些年老太太的亲人先后离世,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,为了养活她那早些年反对跟老头在一起,见钱眼开的势利母亲,老太太在学校做了三十多年的清洁工。
老头对女人说:“你母亲就是喜欢钱,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钱,或许你嫁的人就是我。”女人说:“母亲也是为我好,她欠了很多高利贷,如果我不去帮她还,她早就被人家卖到酒店做皮肉生意,也怪我当时鬼迷心窍为了贪图享乐,以为攀上有钱人就能享清福,顺道帮母亲还债。”
老头叹了一口气,说:“我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,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在一起了吧!”女人哭了起来,也不知道是感叹自己的大半生,还是感慨老头一直把她放在心里上。
女人说:“母亲临死前,一直很内疚,骂自己是混蛋,不该拆散我们,不然我们会很幸福。”老头握起女人的手说:“红,你知道吗?我这些年真的很想你。”老太太回道:“我何尝不是?如果当初不嫁那个土豪,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。”
老头:“我们重新开始吧!”女人撒娇:“你就没什么表示吗?还有,你说过你想要我的第一次,我没有了怎么办?”
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镶着心形钻石的戒指,套在老太太手指上,郑重其事地说:“我想红,并不一定要你第一次红。”
女人感动得热泪盈眶,悄悄在老头耳边絮语:“其实人家还是个老姑娘呢?”老头和老太太相视一笑,牵手回老头的家去验证“红双喜”,月光下他们影子越拉越长……